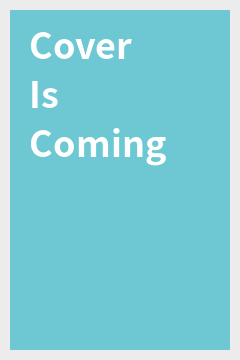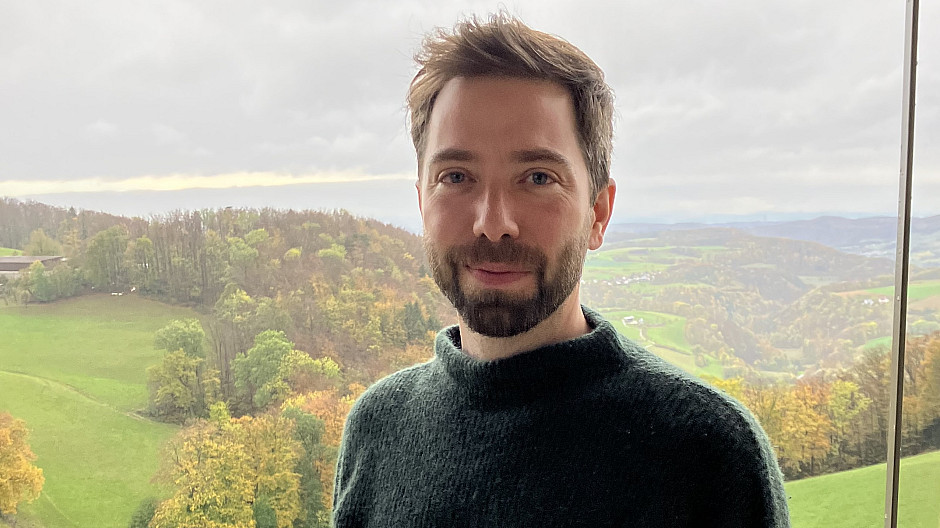內容介紹
★人類醫學史上被遺忘的篇章,徹底改變全人類的飲食科學與公共衛生政策,推薦給喜歡《改變人類醫療史的海拉》(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的讀者。作者經紀公司David Higham Literary Agency的agent最初在作者刊登於《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的一篇文章摘要中發現這個故事,該文章是作者於 2022 年在瑞士Das Magazin雜誌報發表的文章的英文改編版。這篇作品贏得了 2023 年瑞士科學新聞最高榮譽——瑞士藝術與科學學院媒體獎(Prix Média),在瑞士當地引起了巨大關注,竟然是一位外國人來提醒他們這段非凡的國家歷史。隨後,作者決定將其調查出版成一本書。
(以下簡介包含上方提及文章的節錄,字數有點多,各位可用看童話故事的心態來閱讀。一片受古老詛咒籠罩的土地、大膽的治療方法、孤獨的探索、勇敢的英雄、國家幾乎在一夜之間得以重生。甚至還有一個合格的反派角色,支持納粹的瑞士建制派支柱,試圖阻撓主角。)
市售含碘鹽需標示「碘為必需營養素」。究竟是誰發現碘對人體的重要性?
長久以來,瑞士人飽受神秘疾病困擾,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脖子前頂著突出的腫塊(現已知為甲狀腺腫),十分之一的新生嬰兒患有克汀病(cretinism),發育不全。在那個期盼孩子能協助養家的年代,這類嬰兒的出生無異於家庭的負擔。而對十九世紀來到瑞士的遊客來說,這些患者是觀光重點之一。馬克.吐溫在 1880 年記錄了一位英國旅行者的話:「我看到了瑞士主要的景點——白朗峰和甲狀腺腫。現在可以回家了。」甲狀腺腫和克汀病在當時被瑞士人稱之為 Nationalübel,即「國家的災禍」,是十九世紀歐洲最大的醫學謎團之一, 科學家與醫生紛紛湧入阿爾卑斯山區,從地形景致、海拔、大氣電學、融雪程度、日照長短、居民生活習慣等,不放過任何一個細節地尋找疾病可能成因。
1883 年,伯恩大學外科講師海因里希·比歇爾(Heinrich Bircher)博士發表了一份瑞士每個城鎮和村莊的甲狀腺腫調查報告,除了西北邊侏羅山區和提契諾州南部的患者較少,其他地方的病患數都高得嚇人。這份報告似乎更加深了謎團,凱撒奧格斯特村受到嚴重影響,但僅僅十公里外的埃芬根卻沒有。從魯道夫·魏爾肖(Rudolf Virchow)到亞歷山大·馮·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歐洲最偉大的科學家們都曾試圖解決甲狀腺腫問題。然而,解決方案並不是來自大學、醫院或研究機構,而是來自一位名叫海因里希·亨齊克(Heinrich Hunziker)的年輕醫生,他是蘇黎世西部邊緣小鎮阿德利斯維爾的一名家庭醫生。1914 年 5 月,他在蘇黎世醫生協會起立發言時,他已經 34 歲了。他說,每個人都找錯地方了。造成這種症狀的原因不是多了什麼,而是人體缺少了某些東西。
甲狀腺是一個形狀似蝴蝶的腺體,展翅在喉嚨兩側。它產生兩種激素,作用於幾乎每個身體細胞,影響所有的生理機制:從新陳代謝到大腦活動,從體溫到生長。這些激素含有碘化物,而人體無法產生碘,因此為了產生激素,人類必須從飲食中獲取。如果碘不足,甲狀腺會膨脹,以更有效地從血液中過濾碘離子,最終變成甲狀腺腫。兒童如果缺乏這些激素,他們將無法正常長大。媽媽若沒有足夠的甲狀腺素,肚子內的胎兒無法發育,導致出生缺陷。世界上幾乎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碘,海水中的含量尤其豐富,當海水退去時,該元素仍留在陸地上,被植物吸收,被動物消耗並返回土壤,保持穩定的「碘循環」。但在瑞士卻不然。阿爾卑斯山上於冰河時期形成的永久冰蓋,在這十萬年間經歷無數次融化和凝結,帶走瑞士高原表面250 公尺的岩石和土壤,卻從未擴及至侏羅山區和提契諾州南部地區。
亨齊克提出他的理論時,人類才剛發現激素的存在,營養科學發展才剛起步,瑞士土壤的化學成分尚不清楚,直到1964年,巴塞爾外科醫生弗朗茲·默克(Franz Merke)才指出冰蓋的範圍與甲狀腺腫的流行區域完美吻合。儘管如此,亨齊克提出的觀點最終都被證明是正確的。科學家其實早在 1811 年就發現了碘元素,當亨齊克在蘇黎世醫生協會發表演講時,碘已被用於止咳藥、護膚霜、壯陽藥等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治療方法,但亨齊克建議治療甲狀腺腫只需這些治療藥物萬分之一的劑量,並每日攝取。事實上,他聲稱多年來一直在進行微劑量測試,並沒有任何不良影響。在治療期間,甲狀腺腫縮小了;當治療停止時,它又長回來了。瑞士人所需要的只是每天透過食鹽攝取的少量碘。1915年,亨齊克的演講被出版為24頁的小冊子,言簡意賅又單純得令人不敢置信,卻在發表後不久遭到了嚴厲的批評。蘇黎世大學的一位頂尖醫生阿道夫·奧斯瓦爾德(Adolf Oswald)在瑞士最具權威性的醫學期刊上反駁亨齊克的提案。亨齊克不是第一個提出用碘治療甲狀腺腫的人,但所有歷年的實驗終以失敗收場,甚至引發大規模碘性巴塞多氏現象(現稱為碘誘發的甲狀腺機能亢進)。 亨齊克提出每日微劑量碘攝取的概念確實新穎,卻無法有效說服所有人。
在阿爾卑斯山另一處,一位比亨齊克小兩歲的鄉村醫生奧托·貝亞德(Otto Bayard)也在關注這場辯論。他曾在都柏林求學,並曾作為船醫去過中國和印度尼西亞。貝亞德對亨齊克的理論持懷疑態度,但他想知道亨齊克每日微劑量碘攝取的提議是否有效。因此,貝亞德設計一個實驗,他準備了五種不同濃度的碘化食鹽,給甲狀腺腫地區的五個家庭服用五個月,最低濃度為每公斤鹽僅4 毫克的碘。整個冬天患者持續食用碘鹽,當貝亞德春天到村莊複診時,五家人不但沒有中毒,脖子也都變細了。貝亞德率先宣布了他獨自實驗的成果,同一時間,來自大西洋另一端大衛·馬林(David Marine) 在俄亥俄州用碘片治療甲狀腺腫的成功消息傳到了瑞士。貝亞德繼續他的實驗,調整劑量,直到 1921 年底,他收到邀請,在伯恩新成立的瑞士甲狀腺腫委員會上展示他的研究結果。
時間來到1922 年 1 月 21 日舉行的第一次委員會會議,與會者對於碘鹽有效的原因存在分歧,但卻無法辯駁其成效。貝亞德認為應該強制推行加碘鹽,有些人則認為公民應該能自行選擇是否使用它,更有人主張在食鹽供應中祕密添加碘,只有當效果被證實後才揭露給大眾知道。另外,還有一個複雜的情況,按可追溯至中世紀的傳統,瑞士每一個州都擁有其境內鹽銷售的自主權,即使要實施加碘,也無法由聯邦政府下令執行。一如貝亞德後來在手稿中寫道,這是一項「西西弗斯任務」。
然而,與會的一名男子確信這是可以做到的。漢斯·艾根伯格 (Hans Eggenberger) 是黑裡紹 (Herisau) 醫院的首席醫生,黑裡紹是人口稀少的外阿彭策爾州的首府。艾根伯格毫不懷疑亨齊克的理論,前一年的五月,他即向外阿彭策爾州衛生部門提議在食鹽中加碘,據他當時的助手的回憶,他被告知「人民永遠不會允許自己接受這樣的事情」。過去,阿彭策爾人因抵制改革在瑞士聞名,但艾根伯格對他的同胞卻持不同的看法。委員會會議結束三天後艾根伯格返回黑裡紹,他宣佈將在鎮上電影院安插關於碘鹽的講座。在地居民也許是出於好奇心,又或是被這位魅力四射的40歲醫生吸引,當天電影院裡擠滿了人。艾根伯格用當地瑞士德語方言交流,幽默又煽情。他將加碘鹽稱為“全鹽”,與“全脂牛奶”和“全麥粉”相呼應,使其聽起來自然又健康。他擬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州政府「承擔全鹽生產的責任,提供財源,並讓人民在任何販售鹽的地方都可以買到“全鹽”」。僅僅五天時間,他就收集了三千多個簽名。 2月20日,外阿彭策爾州州政府批准生產。兩天後,也就是甲狀腺腫委員會召開第一場會議的一個月後,外阿彭策爾州開始銷售碘鹽。不是政府強制人民服從,而是大眾的要求。
六月,甲狀腺腫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瑞士甲狀腺疾病權威弗里茨·德·奎萬(Fritz de Quervain)教授在不完全了解其作用原理的情況下,準備向整個國家提供碘鹽。他知道委員會即將做出歷史性的決定,這項決定可能會解放國家,也可能殺害無辜人民並摧毀對醫學界的信任。6月24日,委員會正式向各州建議加碘入鹽。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地方做過這樣的事情,這是人類史上第一個食品營養強化計劃,政府首次嘗試透過在食品供應中添加化學物質來改善全體人民的生活。一年之內,加碘鹽就在瑞士17個州販售。到了1930 年,凡是使用碘鹽的地方,甲狀腺腫幾乎都消失了。自 1930 年以來,瑞士出生的嬰兒中沒有一個患有先天性碘缺乏症候群。「國家的災禍」被從這片土地上消失了!巴賽爾新聞報 (Basler Nachrichten)在委員會召開會議後的頭版寫到:「除非所有跡像都被證明是騙人的,否則瑞士今天正站在一個沒有甲狀腺腫的未來的大門前。」這篇文章稱讚亨齊克和艾根伯格是人類的恩人,是醫衛新時代的先驅。
當今社會,碘鹽存放在任何人家中的櫥櫃上,但是為什麼這段歷史不為人所知呢?為什麼這些先驅者的成就被遺忘,證據被擱置在塵封的檔案中?
藥物的推行關乎民眾信任;而民眾信任容易受政治操作。
亨齊克與貝亞德不屬於任何研究單位的背景,讓注重階級的學術圈子顏面盡失;把碘加入鹽中的治療方法也讓藥廠無利可圖。1922 年 7 月 20 日,在甲狀腺腫委員會提出建議加碘鹽後不到一個月,《瑞士醫學週刊》上刊登了一篇異常長的社論,對甲狀腺腫委員會抨擊。該評論的作者尤金·比歇爾(Eugen Bircher)是海因里希·比歇爾(Heinrich Bircher)的兒子,也是阿爾高州立醫院首席外科醫生,他在沒有任何依據的情況下堅持碘性巴塞多氏現象的風險。有一說是因為當貝亞德開始他的實驗時,比歇爾推出了這是一種昂貴的、為期八天的甲狀腺腫治療藥物Strumaval。委員會推出加碘鹽的作法等於擋了比歇爾的財路。比歇爾是瑞士頗具影響力的人物,身材高大,專橫跋扈,是軍隊中的高階長官,據稱他在慕尼黑政變前幾個月的惡性通貨膨脹期間向希特勒提供資金。他周旋於軍隊、學術圈、醫界、媒體、政府,推崇優生學,把詆毀加碘鹽化作自己的政治聲量。直到 1956 年比歇爾去世之前,比歇爾的家鄉阿勞和其權力中心的碘鹽年銷量還不到該州鹽銷量的 10%。 1931 年,瑞士年輕人的甲狀腺腫幾乎已經消失,但在阿勞,95% 的學童仍患有甲狀腺腫大。
現在你仍可以在瑞士找到比歇爾的雕像,卻不見幾個瑞士人認得亨齊克、貝亞德和艾根伯格。1990年,另一位瑞士醫生漢斯·布爾吉(Hans Bürgi)發表了一篇關於被遺忘的碘先驅者的英文論文。那一年,全球只有不到 20% 的家庭使用碘鹽,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因此發起了一項全球運動。如今,全球超過 88% 的人口使用碘鹽。碘鹽的推行被認為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公共衛生措施之一。這是一段從未被詳述的歷史,作者走訪瑞士各城市的檔案室,調閱封存的卷宗,包含艾根伯格未出版的回憶錄、藥廠陰謀論的證據、包羅萬象的私聯通訊、官方的會議紀錄,以及未公諸於世的影像。
歷史總是驚人地相似:令人恐懼的疾病、對新藥物的焦慮、試圖利用群眾恐懼牟利的投機政客、對藥廠利益的質疑等,身在後疫情時代的我們必能感同身受。推薦給對想了解科學、醫學、政治和個體之間如何相互牽制感興趣的讀者。
作者介紹
海外授權
英國(Summit/Simon & Schuster)、德國(Hanser)